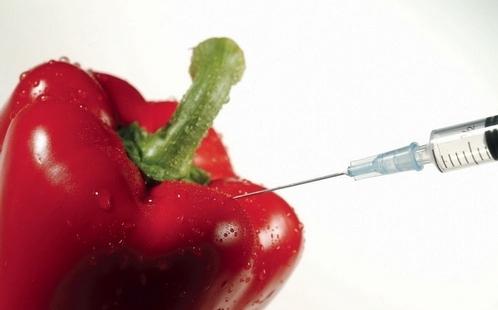北京黑人美容美发广州黑人族群:熟悉的陌生人?北京黑人美容美发
“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来中国,还是要找非洲人合作。”大卫帮了的忙,那些老板也不亏待他,经常会给大卫几百上千美元作为酬劳。有些卫,既然你这么熟悉中国市场,为什么不自己做生意呢?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志刚是研究广州外来移民问题的学者,但他也无法准确统计黑人的数量,因为很多黑人并没有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部门登记备案。坊间流传着另一种未经的说法:广州有大约20万黑人。“因为这里的货物足够便宜,在非洲很畅销。”一个尼日利亚商人说,“我来中国就是为了赚钱。我不知道在哪里,在我看来,广州才是中国的中心。”
大卫是跟着他的非洲学会做生意的。在华南理工大学读书期间,经常有坦桑尼亚商人来找大卫,请他做向导,一起去市场里看货。大卫讲中文很流利,能帮这些非洲商人和中国人讨价还价,老乡爱找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对的信任感:很多非洲商人都吃过中国人的亏,在他们看来,“中国商人太擅长了”。
他的中文名字叫“小吴”,2008年来中国,现在汉语说得很流利,这在广州的黑人族群里不多见。但是除了谈生意,小吴也没什么机会运用他的汉语技能,“本地人不爱和我们打交道。”在宝汉直街的城中村,每当夜幕,霓虹亮起,街头几乎全是黑人,宛如非洲市集。
“一个20平方米不到的档口,要租下来你猜多少钱?”李秋丽伸出两根手指:“20万人民币—这是转手费!租金还要每个月五六千块。”天秀大厦由三栋楼组成,中间一栋是商用,两边两栋本来是住宅楼,后来都被高价租出去开公司用了。即使这样,当年想在天秀大厦租间档口也非常困难。喧闹的市场,汹涌的客流,是广州的中非贸易极盛时期的景观,也是黑人移民“挤走”本地业主的商业能量。
“出现这样严重的质量问题,厂家不负责赔偿吗?”我问大卫。
“我可以跟你说说这些黑人的来历。”大卫说,“有一些黑人是像我这样的留学生,在中国读完书以后发现有赚钱机会,就留下来做生意。更多的是很早就在非洲做生意的商人,他们以前在迪拜、东南亚和拿货,大概2004年到2005年的时候,很多人像发现新一样,发现了中国内地的市场。”
在珠江新城附近的“Sports”酒吧,李秋丽翻着酒水单,点了一瓶红酒。“这是我最近的爱好。”她熟练地瓶塞,“没准哪天有机会做做红酒生意呢。”
“只要你想改变生活,你就能做到。”李秋丽说。
有需求的地方就会有市场,如今在小北一带,大大小小的阿拉伯餐厅有几十家。在天秀大厦、登峰宾馆、陶瓷大厦之类的商贸城里,还能找到很多为黑人提供家政服务、机票预订、货币兑换、美容美发等常用业务的店面。
大卫追求李秋丽用了三个月,起初没少碰钉子。“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活泼、漂亮,就问她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她回答不行。后来我才知道,东方女人喜欢含蓄,追她们需要多些时间和耐心。”大卫开始动脑筋,在校园里地制造“偶遇”。吃饭的时候,李秋丽能看到大卫,买东西的时候又能看到他,站在宿舍阳台上看风景,这个黑黑的小伙子还是会出现在视野里,李秋丽开始对他有了兴趣。
所以等到在广州读大学时,她终于有机会离开父母的视线,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裙子能穿多短就穿多短!”李秋丽暗暗发誓,要彻底改变已经被长辈铺设好的人生轨道。“在家里我妈妈从来不让我穿超短裙,从来不让我穿吊带背心,从来不让我化妆,从来不让我做的好多事情,我到大学里都赶紧做。”她在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国际贸易,每天打扮得很摩登,在校园里招摇过市,梦想做个成功的女商人,靠自己努力赚很多很多钱—这是当年她能想到最出格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李秋丽在珠江新城的高档小区买了房,经营一家电器贸易公司,晚上收工后可以到酒吧里喝酒,和来自世界的朋友们聊天。
“好吧。”李秋丽回答。
阿强说的这片地方属于越秀区,聚集着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客商,他们大多肤色黝黑,身形壮硕,几乎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国际贸易。珠三角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之一。来自非洲的黑皮肤的商人们在广州林立的商贸城里穿梭,批量订购服装、电器、日用品甚至汽车和摩托车零配件,运到非洲去卖。
房产中介简姐说:“他们太吵,又脏,我不会讲外语,管理很麻烦。”黑人一般睡到中午才出来吃饭,下午逛市场、谈生意,然后和朋友、喝酒到深夜。黑人和广州本地人“习性”不同,导致黑人聚居的街区被形象地称为“巧克力城”—广州人眼中的城中之城。
“当时我以为他是有女朋友的,因为有次去他宿舍的时候看到门口有女孩子的鞋子。”有两个广外的女孩经常去找大卫,李秋丽以为其中一个是他女朋友,心想黑人果然不可靠,有女朋友了还说喜欢我。
这座36层高、镶满绿色玻璃的大厦,是小北的地标建筑,也是广州最著名的中非贸易集散地。大厦里密布的几百家商铺和写字间,大部分经营者洲人,剩下的也是和非洲人做生意的中国老板。天秀大厦门前是主干道的交叉口,高架桥和铁轨纵横交错,有个造型扭曲的天桥连接各个口,天桥上有举着“PHOTO”牌子的摊贩。很多黑人来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站在天桥上,以天秀大厦为背景拍张照片,寄给远在非洲的家人,告诉他们广州有多么繁华,遍地是金,发财指日可待。
阿里来自也门,这是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国家,隔着狭窄的红海和亚丁湾,与非洲毗邻。在广州,因为各种巧合,阿里本人也像他的国家一样,成了阿拉伯世界里连接中东和非洲的枢纽—在天秀大厦一层的沙巴清真餐厅里,四百多平方米的空间坐满了边吃东西边谈生意的穆斯林,除了几个中国服务生,餐厅里几乎全是黑皮肤。
“这里是黑人的据点,很少有中国客人来吃饭。”阿里的助手卢小姐说,“但是我觉得我们餐厅的食物很好吃,你也可以尝尝看。”餐厅的菜单上有几十种地道的清真菜品,价格不便宜,但确实很受附近的黑人欢迎。开业至今,沙巴餐厅的生意一直很红火。
天秀大厦矗立在雨中。
吃在广州
“听说非洲黑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你当心被骗哦。”女伴提醒李秋丽。
在2007年的天秀大厦,刚刚毕业的大卫和李秋丽赚到了第一桶金:这是来自坦桑尼亚的订单,为一条正在修建的几十公里长的公提供灯。大卫在广东中山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厂商,这笔生意为他打通了与非洲国家合作的门。后来碰到总统,大卫还接了一单订制几十万件宣传T恤和围巾的生意。
“他们根本不会承认这种事,反而会责怪我为什么不验货。”大卫很无奈,说在非洲做生意,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会签订规范的合同,双方都是基于淳朴的互相信任来合作,这种商业习惯到中国来很容易吃亏,有了麻烦也不愿诉诸法律。那笔生意让大卫亏了不少钱,最后厂家同意提供一些电视机零件给大卫,让他一边维修一边折价清货。
下一条:赵欢:短期大盘或将反复拉锯震荡
“广州是个大城市,有很多外国人。”在白云机场开往广州市区的出租车上,司机阿强指着牌向我介绍:“这边出去是三元里、广园西,往前走到环市中、小北,都是黑人的地盘。”
淘金年代
李秋丽的丈夫大卫来自坦桑尼亚,31岁,2002年拿到中国的学金来广州留学,两人是在学校里的派对上认识的。黑人表达感情往往很直接,在小北一带黑人聚居的街区,中国女孩子很容易遇到黑人小伙子搭讪。“他们经常开口就问你要电话号码,或者直接说我喜欢你,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之类的话。”李秋丽说,她和身边的女伴都知道不能轻易答应黑人的邀请,否则被纠缠起来很麻烦。
大卫和李秋丽也选择天秀大厦作为生意的起点,两人租下了大厦里的一间档口。那已经是2007年了,随着黑人的大量进驻,天秀大厦的本地业主开始纷纷搬走,以前定位商住一体的高档楼盘,逐渐变成非洲商人的贸易中心。
不过2000年天秀大厦落成时,业主大都是中国人,广州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黑人。“我是天秀大厦最早的租户。”沙巴餐厅老板阿里·伊士麦尔莱说,他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五年,如果可能,他希望永远不要离开中国,“我会在这里待到死为止。”
围绕着天秀大厦的小北、登峰街、环市中等街区,一直延伸到三元里、广园西一带,聚集了无数黑皮肤的商人。“2008年以前最多的时候,常住广州的黑约有两万人,流动人口可能还有六万人左右。”
阿里原本经营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曾经在印度尼西亚待了十年,十五年前第一次来广州,在陶瓷大厦租了一间档口批发服装。2002年天秀大厦的商铺开始营业,距离陶瓷大厦只有五百米,阿里敏锐地意识到了商机。“陆续有一些非洲商人到这边来做生意,因为在广州拿货比更便宜。做生意的人需要一个见面谈话的地方,需要一起吃饭,有饭吃才能稳定下来。”越来越多的黑人客商来到广州,而能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链条还未建立起来。当时整个广州的清真餐厅都很少,阿里就因为找不到习惯的食物而倍感痛苦,他决定自己开家餐厅。
说起往事,大卫哈哈大笑:“穆斯林才可以娶四个,我信,只能有一个老婆。”再次的时候,他很慎重,先请李秋丽去酒吧喝酒,然后请她去宿舍坐坐,放浪漫的音乐,两人又喝了点酒。估计气氛差不多了,大卫说:“请你相信,我真的没有女朋友……”
上一条:中国技术贸易年逆差约150亿美元
而她生活最大的改变却连自己都没想到:嫁给一个黑人。
而按照阿里的说法,商人们发现有利润的地方同时有吃有喝,就会蜂拥而至,迅速建立起各自民族和种族的商业圈。“哪里有钱赚,我们就到哪里去。”阿里已经在浙江义乌开了新的餐厅,他雇佣的中国员工超过150人。
珠江新城地处广州的CBD,紧邻繁华的天,酒吧里坐满了老外,很多人认识李秋丽,过来跟她打招呼:“嘿,萨米拉!”他们叫她的英文名字,李秋丽也热情地和对方握手、拥抱。
“看不出来吧,我是潮汕人。”李秋丽说,父母从小教育她,女人要以家庭为重。在民风保守的潮汕地区,同龄的女孩们通常都在家相夫教子,很少有人像李秋丽这样外出打拼。“你知道我们家乡的传统有多恐怖吗?”李秋丽说,“潮汕人家一定要生男孩,我有个表姐嫁了人,已经生了三个女儿了,还在拼命生,非要生个男孩不可。她现在一怀孕就跑去检查是男是女,女孩就打掉,现在已经打到第七胎了,吓。”李秋丽有三个弟弟,都在潮汕老家待着,“二十几岁了还活在我爸的翅膀底下。”这种“被掌控”的生活方式让李秋丽“随时受不了”。
“本来在市场里看好的货,交完定金,等货发过来发现换成了另一种,或者是发过来的货物数量不对。甚至有些中国商人收完定金迟迟不发货,等你再去看的时候,他的档口都不见了。”
“我们晚上都不去那边,全是鬼佬。”在的士司机阿强看来,即使取个中国名字,黑人也还是“鬼佬”。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称谓背后,是外来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我们的房子一般不租给黑人。”
从2005年到2007年,那是最好的时代。在对中国意义非凡的2008年到来之前,云集在天秀大厦的商人们快乐地数着口袋里的钱,每个人对未来都信心满满。“一条牛仔裤进货价2美元,运到非洲卖5美元,利润是150%,我认识的很多客户一单就订几万条。”大卫说,生意最火爆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钟,商人们要排队进天秀大厦买货,每个档口前都挤满了人。
类似的事情每天都在市场里发生,大卫慢慢也长了心眼,“我不再单纯相信档口老板的话,大额生意成交之前,我一定会去看他们的工厂,如果那个工厂看起来不够好,我就不做生意。”大卫说,但是有些貌似可靠的供应商也会出问题。有一次他订购了两千台电视机,因为是熟悉的厂家,大卫没有认真验货。两千台电视机运到非洲才发现,“最多有四百台能用,其他都是垃圾。”
黑色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