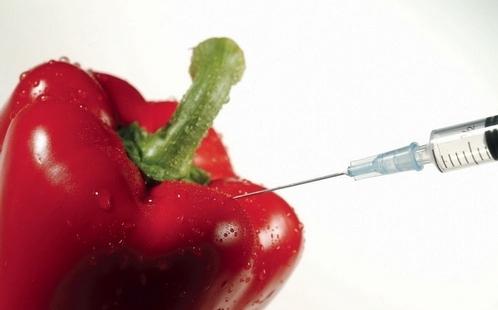我爱我的祖国(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爱我的祖国(我与新中国·庆祝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对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风雨雨、跟着党和国家一起走过艰辛历程的人来说,更能体会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正确道路、埋头苦干的历史意义,这种实干兴邦的奋斗精神感染了我。为了美丽理想,虽历尽沧桑,但是壮志未改,在余霞满天中,我要发挥余热,报效祖国和人民。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仿佛转瞬间,我已经跨过一个世纪,进入一百零五岁了。回首百年岁月,既如梦如烟,又历历如在眼前。自上世纪三十年代投身革命起,我在出生入死的地下党工作中得到磨炼;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我亲见一代读书人于艰苦卓绝中的气魄和风骨,也真切听到人民怒吼的心声和越吹越响的斗争号角;新中国成立后,在如火如荼的国家建设中,我从头开始学城市规划、学工程管理;改革开放春雷滚滚,在日新月异的生活变迁中,我和所有人一样见证这个国家的扬眉吐气;有幸跨入新世纪,我更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一个民族实干兴邦的奋发崛起……
如果说作为一个百岁老人,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和认识,那可能就在于,我对“新中国”三个字沉甸甸的分量有着别样的体会,也更能感受到置于百年沧桑的历史里,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这一喜庆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其间有太多值得记取的故事和经验。
贡献社会、服务人民是我一生志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叫我作家、老作家,我还是觉得受之有愧,我是六十年前很偶然地开始创作的,直到今天,也只能算是个业余作家。
记得那是国庆十周年前夕,《四川文学》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盛情难却之下,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老三姐》。文章在《四川文学》登出后,被《人民文学》转载,竟引起中国作家协会领导的注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把我请到北京,开门见山地说:“看你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积累;看你的文笔,能够写文学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我们要求你参加进作家的队伍里来。”我说自己本职工作很忙,邵荃麟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一点倒真的打动了我。能做两份工作,对社会特别是对青年读者能多一份贡献,的确是好事。于是我回到成都,便这样开始写作了。
但那时我的本职工作实在是忙,几乎没有时间来写。《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派编辑周明来成都找我约稿。周明见我的确忙,也不催着我交稿,而是留在成都,趁我休息时来找我,说是想听我摆一摆过去革命斗争的龙门阵。这好办,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故事我随便一摆就是好几个,周明马上抓住说:好,就这几个故事,你按你摆的写下来就行。就这样,《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一篇一篇地发表出来。
写作打开了我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那段惊心动魄的革命生活虽然已经过去,但它铭刻着苦难艰辛的历史,积淀着革命者的智慧与意志,闪耀着无数人的理想与信念,这些都不会随时间而逝去,也不该被我们忘记。它是我们的来路。更何况,那些熟悉的、牺牲了的同伴朋友,常常来到我的梦中,和我谈笑风生,叮嘱我、呼唤我、鼓励我……一种感情在催促我,让我欲罢不能。我知道,让他们在我的笔下“重生”,让后来人知道他们的信念与精神,是我的责任所在。
1960年创作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是我文学经历中最难忘的事情之一。创作缘由是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大事:我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失散二十年的女儿。二十年前的1941年,我和爱人刘惠馨一同在湖北恩施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我们的女儿才出生一个月,刘惠馨就因叛徒告密,不幸被特务逮捕。她和一同被捕的何功伟同志在狱中英勇斗争、坚贞不屈,后来从容就义,我们的女儿从此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各种场合打听其下落,却毫无结果。后来通过组织查找烈士遗孤,湖北省公安厅组织专案组,经过一年多曲折历程,终于把我的女儿找到了,她那时已经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一年级。巧合的是,何功伟烈士的儿子也同时在这个学校读一年级!我得知这个消息后,急忙飞往北京,抱着两个烈士的孩子,潸然泪下。
这件事在四川一时传为佳话。沙汀等文学界的朋友鼓励我,以此事为引,写一部长篇小说。虽然那时我工作仍然很忙,但我已经从感情上进入角色,把烈士们革命斗争的事迹彰显出来,这是我念兹在兹、一刻也不曾忘却的事。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动起笔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终于完成这部《清江壮歌》。小说中有关贺国威和柳一清的许多细节,都取自何功伟和刘惠馨两烈士的实际斗争生活。与其说这是我写的长篇,还不如说是烈士们用鲜血写就的。
这部小说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后来武汉日报也开始连载,没想到竟获得那么多读者喜欢,我收到大量的群众来信。四川大学的柯召教授告诉我,他每天晚饭前必去取成都晚报,看连载的《清江壮歌》,他说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如此。这部小说的连载,也引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注意,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开印就是二十万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还先后全文连播。《清江壮歌》奠定了我对革命文学的信心,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人民对革命先烈的历史事迹渴望有更深入的了解,革命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光与热一样,永远为人的心灵所需要, 也一定能发挥凝神聚力的作用。
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作家都会自觉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他们从自己切身体会中知道,离开了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没有作家的存在,更说不上创作,即使创作了,也不为广大人民所欢迎。”我还记得,1982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时,在国际作家会议上做了此番发言,这是我创作的肺腑之言,也是我对许多作家同行们的观察所得。
在我生活过的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多少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进行的革命是多么悲壮,又是多么炫丽!有多少慷慨悲歌之士,多少壮烈牺牲之人,多少惊天动地之事,都可以作为我们加以提炼与展现的文学素材。遗憾的是,我写出的只是这丰富素材中的一小部分。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时代永远是需要文学和作家的。如果我们拿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精品来,人民永远是欢迎的。因此,我始终怀抱乐观的态度关注文学界。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必将有大量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精品涌现出来,前提就是作家们自省、自强,“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坚定走一条雅俗共赏的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之路。这也是我愿意为之摇旗呐喊、终生不改的文学志向。
一百岁的时候,我的长篇回忆录《百岁拾忆》出版了,那时,我为自己定下一个“五年计划”,希望能继续我的文学创作。五年里,我完成回忆录《人物印象——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和小说《夜谭十记》续集《夜谭续记》,都已先后交付出版社。我在一百零五岁的自寿诗里写道:“三年若得兮天假我,党庆百岁兮希能圆”,朋友们笑说,这是我的第二个“五年计划”。
笑谈归笑谈,但这真的是我的梦想。还记得1938年,我在入党申请书上郑重其事地签下“马识途”而不是本名“马千木”,因为我确信自己找到了正确的道路,老马识途了。一晃八十多年过去了,对我们这些经历过风风雨雨、跟着党和国家一起走过艰辛历程的人来说,更能体会当下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正确道路、埋头苦干的历史意义,这种实干兴邦的奋斗精神感染了我。为了美丽理想,虽历尽沧桑,但是壮志未改,在余霞满天中,我要发挥余热,报效祖国和人民。
(作者为著名作家)
- 标签:
- 编辑:刘柳
- 相关文章